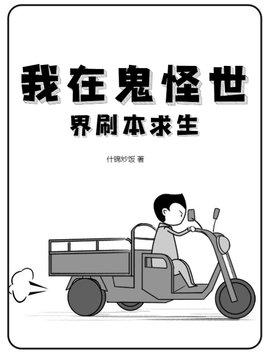大雨文学>大明:入仕从师爷开始 > 第31章 丹房惊变(第1页)
第31章 丹房惊变(第1页)
严楼穿着簇新的绯色官服,踏入职方司武库署。
檐角冰棱尚未化尽,廊下排列的火绳枪在晨光中泛着冷光,枪托上的“京营”刻字清晰可见。他蹲下身,指尖抚过枪管上的膛线——七道刻痕,与三日前在浙江解送的倭寇火器分毫不差。
“大人,这是京营去年新造的鸟铳。”武库署主事王顺低头哈腰,袖口绣着的獬豸补子皱成一团,“共五千杆,上月刚拨付蓟州镇。”
严楼站起身,目光锐利地看向王顺:“既已拨付蓟州镇,为何浙江会出现同样制式的倭寇火器?而且,这京营新造鸟铳,怎会流入敌寇之手?”王顺额头瞬间冒出冷汗,双腿微微颤抖:“大人,这……其中定有误会,小的实在不知啊。”
“不知?你身为武库署主事,职责所在,如今这般状况,你难辞其咎。”说罢,他环顾四周,心中思索着这背后或许隐藏着巨大的阴谋,此事绝不能轻易放过,必须深挖到底。
严楼抽出腰间短刀,在枪管上轻轻一刮,铜锈剥落处露出底下的暗纹:“京营火器刻纹该是五道,何时改了制式?”王顺的喉结剧烈滚动,额角渗出细汗:“许是工匠手滑……”“手滑?”严楼冷笑一声,从袖中掏出倭寇火绳枪的残件,“倭寇手中的枪,倒和贵署的‘手滑’之作一模一样。”
王顺扑通跪地,膝盖撞在青砖上发出闷响:“大人明鉴!小的只管造册登记,实在不知……”严楼盯着对方发抖的指尖,想起裕王案中被灭口的严州商行掌柜。他站起身,目光扫过整排火器:“把近三年的造枪账册,全搬去值房。”
戌初时分,武库署值房烛火通明。严楼翻看着账册,朱砂笔在“嘉靖四十年十月,造火绳枪五千杆,用银三万两”处划出粗线。数据没错,但京营实际入库记录只有四千五百杆——平白少了五百杆。他捏着账册的手骤然收紧,纸页发出细碎的撕裂声。
窗外突然传来梆子声:“天干物燥,小心火烛——”话音未落,车厢方向腾起橘红光焰,浓烟顺着夜风灌进制图房。严楼猛地起身,账册摔在桌上:“走水了!”
他冲出门时,只见武库署后墙火光冲天,几个太监抱着水桶奔跑,为首的中年太监腰间挂着司礼监腰牌。严楼刚要指挥救火,忽见火光中有人影窜向档案库——那里存放着京营火器的模子和图纸。
“守住档案库!”严楼抽出绣春刀,转身时却见刚才的司礼监太监突然变向,直扑他而来。火光映着对方袖口翻出的金属光泽,严楼本能侧身,淬毒匕首擦着脖颈划过,在肩甲上擦出一溜火星。
“找死!”严楼旋身挥刀,刀背重重磕在对方手腕上。匕首落地的瞬间,他看清了对方耳后黄豆大的黑痣——那是东厂“影子”的标记。太监狞笑一声,从怀中掏出火折要掷向档案库,严楼飞脚踢中其手腕,火折掉进雪堆,腾起一阵青烟。
此时救火的兵卒已赶到,严楼扯下对方腰牌,发现背面刻着“乾清宫”三字。他蹲下身,掀开太监衣襟,心口处刺着一条昂首的五爪小龙——这是只有近侍才能纹的皇家暗记。
火势扑灭时,档案库已烧去半面墙。严楼在焦黑的残垣中找到半张未燃尽的图纸,上面用朱砂圈着“火绳枪刻纹改良”字样,落款是“御用监掌印太监吕芳”。他的手指骤然冰凉——御用监掌管宫廷用度,怎会插手京营火器?
回到值房,严楼盯着桌上的账册和毒匕首,耳边回荡着王顺被带走前的哭喊:“大人,上个月有太监来提枪,说奉了……奉了内廷的令!”他抽出倭寇火绳枪残件,与京营火器并列,七道刻纹在烛火下像七道伤疤。
子时三刻,徐阶的马车悄然停在武库署后巷。严楼将毒匕首和腰牌递过去,老人的指尖在“乾清宫”刻字上停顿良久:“吕芳是裕王旧党,当年曾替他在江南采办丝绸。”他镜片后的目光骤然冷冽,“火器刻纹改良,是裕王案中账本里提过的交易内容。”
严楼猛然想起,裕王账册里确实有“倭国献刻纹之法,换丝绸千匹”的记载。原来早在三年前,内廷就已将改良技术泄露给倭寇,难怪对方火器与京营制式如出一辙。他握刀的手背上青筋暴起:“所以他们既要灭口,又要烧毁档案,生怕我查出刻纹的关联?”
徐阶将腰牌收入袖中:“吕芳背后是端妃娘娘,而端妃……”老人没有说下去,只是拍了拍严楼的肩膀,“京营火器案,已不是单纯的通倭案了。”
更深露重,严楼站在武库署门前,望着东方渐白的天际。袖中图纸上的刻纹仿佛活过来,化作倭寇枪口的青烟,又变成浙江百姓的血泪。他忽然明白,裕王案不过是冰山一角,当火器刻纹将内廷与倭寇串联,背后牵扯的,是整个宫廷的权力暗战。
次日卯初,严楼带着残件和账册闯入兵部大堂。尚书霍冀拍案大怒:“严佥都想诬陷内廷?”严楼将毒匕首拍在桌上:“昨夜救火太监,是东厂影子,心口纹着五爪小龙。”他扫过堂下色变的官员,“若诸位觉得此事与兵部无关,严某这就去午门请旨,开棺验看浙江解来的倭寇尸体——他们手中的枪,每一道刻纹都在打大明的脸!”
霍冀的手在桌下紧握成拳,半晌才挤出一句:“准你彻查武库署。”严楼知道,这是对方妥协的信号。他转身时,阳光正穿过雕花窗棂,照在墙上悬挂的《平倭图》上——画中明军的火器,枪管光滑如镜,没有半道刻纹。
走出兵部时,严楼摸了摸胸口的伤疤。那是昨夜与太监搏斗时被匕首划伤的,此刻还在隐隐作痛。他抬头望着紫禁城高耸的宫墙,忽然想起徐阶说过的话:“东南倭患易平,朝堂心患难除。”如今看来,这颗“心患”,早已从朝堂渗入内廷,像毒瘤般长在大明的命门上。
他摸了摸袖中未燃尽的图纸,上面“吕芳”的名字已被汗水洇开。不管背后是端妃还是更上位的势力,这道刻纹,他刻定了。
丹房的火,不过是个开始,而他严楼,偏要在这惊变中,剜出藏在暗处的毒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