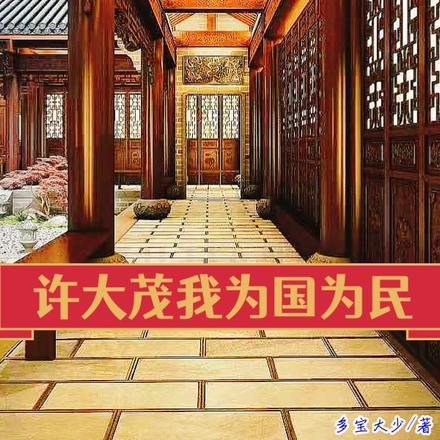大雨文学>大明:入仕从师爷开始 > 第34章 皇子坠马(第1页)
第34章 皇子坠马(第1页)
{西苑猎场层林尽染,金黄的银杏叶在秋风中簌簌飘落,铺就一地锦绣。皇室宗亲、文武百官齐聚于此,参加一年一度的秋狩大典。严楼身着飞鱼服,腰佩绣春刀,站在文官队列里,目光却不时扫向远处奔腾的马群。他心里惦记着军器局新造火器的试验进度,对这场皇家狩猎本没多少兴致。
忽然,远处传来一阵惊呼。严楼抬眼望去,只见一匹黑马发疯似的狂奔,马背上的三皇子朱厚熜身形不稳,随着马的剧烈颠簸摇摇欲坠。周围的侍卫纵马追赶,却因黑马速度太快,一时难以靠近。严楼心一紧,顾不上许多,抽出绣春刀,割断缰绳,飞身上马,向着黑马冲去。
马蹄扬起的尘土弥漫,严楼凭借精湛的骑术,逐渐拉近与黑马的距离。就在三皇子即将被甩落的瞬间,他看准时机,猛地一夹马腹,侧身探出手臂,一把抓住三皇子的腰带,将其从惊马上拽了过来。两人重重地摔在草地上,严楼用身体护住三皇子,手臂擦过地面,划出一道血痕。
众人围拢过来,三皇子面色惨白,紧闭双眼,额头上满是汗珠,左腿膝盖处鲜血汩汩涌出,染红了绣着金龙的裤腿。严楼顾不上自己的伤,撕开衣角,迅速为三皇子包扎止血。他在现代刑警队时,参加过无数次野外救援,战场止血法早已烂熟于心。用力按压伤口、缠绕布条打结,每一个动作都干净利落。
“严佥都,您这是……”一旁的太医瞠目结舌,看着严楼用如此“粗暴”的方式处理伤口,满脸不可思议。
“先止血,否则皇子有性命之忧!”严楼头也不抬,手上动作不停,“去拿干净的布和烈酒来!”
很快,侍卫送来布和酒。严楼用酒清洗伤口,三皇子疼得浑身一颤,却始终未吭一声。清洗完毕,严楼又重新包扎了一遍,确保伤口不再出血。这时,太医们才回过神来,上前查看。
“严佥都,此举不合医理啊。”为首的老太医捻着胡须,眉头紧皱,“伤口应先用草药敷治,怎能用烈酒冲洗,这岂不是让邪气入体?”
严楼站起身,看着太医们,目光坚定:“太医大人,战场上受伤的将士,若不及时止血、清洗伤口,伤口溃烂,神仙也难救。烈酒能杀菌消毒,保皇子伤口不腐。”
太医们面面相觑,显然不认同严楼的说法,却又一时找不到反驳的理由。
三皇子被抬回营帐,安置在床上。他虽已昏迷,但呼吸平稳,脸色也渐渐有了些血色。严楼守在床边,一刻也不敢松懈。太医们在一旁商议,摇头叹气,认定三皇子“邪气入体”,情况危急。
“当务之急,需用童男童女的纯阳之气,驱散皇子体内邪气。”老太医神色凝重,向在场的官员提议。
“荒唐!”严楼忍不住出声,“这是什么歪理?三皇子只是摔伤失血,好好调养便能康复,怎能用如此残忍的法子?”
“严佥都,这是我太医院历代相传的疗法,自有其道理。”太医们纷纷出声反驳,指责严楼不懂医术,胡乱插手。
严楼心急如焚,他知道,所谓用童男童女驱邪,不过是封建迷信,弄不好还会害了无辜孩子。可太医们固执己见,又都是宫中老人,在皇室宗亲中颇具威望。他看向床上昏迷的三皇子,心中暗下决心,绝不能让这种荒唐事发生。
“诸位太医,若依你们所言,用童男童女驱邪,万一皇子病情加重,你们担得起这责任吗?”严楼目光扫过太医们,字字掷地有声,“我虽不懂医术,但在浙江抗倭时,见过无数重伤濒死的士兵,用我这法子救回了不少人。不如给我三日时间,若三皇子病情不见好转,我愿以死谢罪!”
营帐内气氛紧张,众人都望向严嵩和徐阶,等待他们表态。严嵩眯着眼,不置可否;徐阶微微点头,目光中带着一丝赞许:“严佥都既有把握,不妨一试。只是关乎皇子安危,切不可掉以轻心。”
接下来的三日,严楼日夜守在三皇子床边。他让侍卫找来干净的纱布,每天用淡盐水为三皇子清洗伤口,更换包扎。又吩咐御膳房准备营养丰富的膳食,督促三皇子服下。三皇子在第二天便苏醒过来,精神也逐渐好转。
“严佥都,多谢你救我。”三皇子靠在床头,看着忙碌的严楼,眼中满是感激。
“殿下言重,这是臣分内之事。”严楼微笑着说,“殿下只需安心养伤,不日便可痊愈。”
三日后,三皇子已能下地行走,伤口愈合良好,没有丝毫感染迹象。太医们见状,虽心有不甘,却也不得不承认严楼的方法有效。
“严佥都,看来是老夫等迂腐了。”老太医向严楼拱手致歉,“不知这盐水清洗伤口之法,是何医书所载?”
严楼笑着摇头:“此乃民间土方,臣偶然所得。医术之道,本就该博采众长,不拘泥于古法。”他心里清楚,这“土方”不过是现代医学常识,可在这封建王朝,还是不要说得太明白为好。
秋狩大典结束,严楼护送三皇子回宫。夕阳的余晖洒在紫禁城的琉璃瓦上,映出一片金黄。三皇子看着身旁的严楼,若有所思:“严佥都,你不仅火器改良之术了得,这救人性命的本事也让人佩服。日后若有需要,尽管开口。”
严楼跪地谢恩,心中却在盘算。此次救了三皇子,算是在皇室中结下一份善缘。但他深知,朝堂之上,波谲云诡,这不过是漫长斗争中的一个小插曲。回到值房,严楼铺开火器改良图纸,烛光下,他的眼神坚定。三皇子坠马一事虽已平息,可他与传统守旧势力的较量,才刚刚拉开序幕,为了大明的未来,他定要在这重重阻碍中,闯出一条路来。